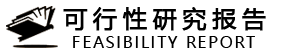更新时间:2018-03-19 09:48:01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从短期看,生产率减速拖累了全球GDP增速,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艰难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全球生产率减速有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将大大降低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水平。
全球生产力是推动全球增长的关键动力。而生产率是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如果相同的投入获得了更多的产出,则表明生产率提升。在生产率分类中,最重要的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指标。其中,劳动生产率是产出与劳动投入量之比,它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人均资本和资源存量,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生产经验,以及知识技术进步等;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则是产出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它主要反映了技术进步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从短期看,生产率减速拖累了全球GDP增速,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艰难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全球生产率减速有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将大大降低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下降,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较大的分化。我们计算了典型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变化。其中,发达国家选取了G7(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韩国;发展中国家选取了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尼、越南、墨西哥。
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减速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统计数据以来,各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年度间起伏波动较大,但从5年平均的趋势线看,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波动中逐渐走低。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呈现以下四大特点。
第一,劳动生产率增速纷纷进入史上的最低区间,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最低值。例如,2011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为-0.17%,为历史第三低,前两次低值分别出现在1974年和1982年,5年平均增长率在2013年创出史上最低值。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在2008年以后都出现了史上年度最低值。
第二,多数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都低于2%。从5年平均增速看,德国从2000年、加拿大从2001年、法国从2003年、日本从2004年、英国从2005年及美国从2006年相继跌入2%以下的低增长区间。而意大利更是早在1996年就跌入了2%以下,甚至在2007年至2010年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劳动生产率低于2%的增速,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4%水平甚至更高的增速相比,下跌了一半还多。不过,韩国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例外,其劳动生产率平均值虽也逐年下行,但一直都高于2%。
第三,这轮劳动生产率下降持续时间很长,发达国家基本上呈现单边下行趋势,没有出现连续2年以上的回升。例如,美国史上最长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发生在1963年至1979年,一共持续了16年,期间还有短期反弹,但美国这轮下降开始于2002年,目前已超过15年,已逼近史上最长时期。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减速持续时间则更长,法国始于1984年,日本始于1989年,德国始于1993年,意大利始于1995年,加拿大始于1999年,澳大利亚始于2000年。2014年以来,这些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很低水平上趋于稳定,英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甚至出现了小幅回升,但整体仍然看不到劳动生产率触底反弹的迹象。
第四,不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变化原来并不同步,但本轮减速趋势大致同步,各国走势大体趋同。
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变化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各国劳动生产率分化严重,走势很不相同。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走势大致分为两类。一部分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例如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虽有所放缓,但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6%以上,在全球是“一枝独秀”;印度则前低后高,2004年以来一直超过5%;越南则呈“U型”变化,2012年以后也一直在5%以上。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很高的。印尼进入新世纪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速逐渐走高,2010年代以来基本保持在4%左右。墨西哥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在2%以下,新世纪以来呈“U型”变化,2008年至2010年出现负增长后,劳动生产率增速有所反弹。但另一部分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很低,近年来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巴西增长率呈“倒U”变化,2009年掉头向下,2014年以后一直是负增长;南非在2008年以后一直下降,2013年以后一直是负增长;俄罗斯则从2005年超过6%的水平掉头向下,2015年起出现了负增长。这轮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劳动生产率负增长不但持续时间较长,而且程度也较深。例如,巴西在2016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6%,是新世纪以来的最低值。
第二,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生产率变化基本同步,但中小型国家走势相对独立。从变化趋势看,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均在2008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此后逐渐下滑,到目前尚未出现触底反弹的迹象,其变化趋势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基本相同。但越南、印尼、墨西哥等国劳动生产率走势非常不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它们的影响不大,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增速都普遍上扬。
生产率减速与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发展形成悖论
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全球看还是从主要国家看,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减速主要是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减速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是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从当年增长率看,金融危机初期的2008年和2009年,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出现了-1.0%和-2.4%的大幅度下降,此后在2010年和2011年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2012年之后又出现了停滞和下降,尤其是2015年和2016年,连续出现-0.7%和-0.5%的负增长。据此测算,2016年全球全要素生产率仅相当于2007年的96.9%,远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从全球5年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看,从1990年代初到2005年经历了一个上升周期,2005年达到最高值1.1%,此后进入了一个下降周期。2007年之后近10年的时间基本处于负增长的状态。2008年至2016年,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0.4%,与1999年至2007年年均0.9%的增长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其中,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逐渐趋同,并接近零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初几年,美国、欧洲、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较大,但2014年后三大经济体的差异缩小和变化趋同。2009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仅下降0.3个百分点,欧洲四大国和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降幅都超过3.5个百分点,德国甚至达到了-5.0%水平。2010年至2014年,各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从2015年开始,各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趋于一致,最高值与最低值差距不超过1个百分点。整体来看,2008年至2016年,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0.4%的年均正增长,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最抢眼。其次是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年均零增长,再次是美国和德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0.1%,其他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降幅均超过0.5%。
与此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中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很大,一部分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但另一部分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则出现了较大的负增长。这与劳动生产率变化大致相似。
虽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也出现减速,增速由2007年的8.2%骤然下降到2008年的4.1%,但此后各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比较平稳,一直在3.3%以上,2008年至2016年年均增速高达4%,不但是全球主要大国中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而且变化比较平稳,在全球经济中明显是“一枝独秀”。印度仅次于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位列第二,其全要素生产率除2012年为负增长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2008年至2016年年均增速为1.4%。更重要的是,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自2012年开始稳步上升,2016年为2.4%,仅比中国低1个百分点,而2011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于中国约3个百分点。印尼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小,年均增速为0.6%,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
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较大,且处于整体下降趋势。其中,巴西年均下降1.7%,在所研究的国家中降幅最大,发生在2015年前后而非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南非和墨西哥全要素生产率均多年出现负增长,年均分别下降1.3%和1.2%。越南虽然年均下降0.3%,但下降主要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掉头向上,保持了一定的正增长。
从理论上看,产业革命有助于提升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新一轮全球科技产业革命蓬勃展开,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却出现负增长,两者走势背道而驰,出现了明显的悖论。
原有统计方法会低估新经济状态下的生产率
当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出现,经济发展模式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不断涌现,若沿用原有的统计方法,很容易低估生产率。
例如,从产出看,一是新经济产生了很多新兴服务业。一方面,服务业本身“无形”特征决定了其比制造业更难统计;另一方面,很多新兴服务业,如知识经济、数字化经济等,并不能被传统统计方法归类,因此统计时可能被遗漏。二是互联网搜索、电子邮件服务、云盘存储等新经济一些模式多为免费使用,很难纳入GDP统计。三是新经济的一些服务采取非货币化交易,如共享房屋、共享汽车等,交易双方在相互使用对方服务时,往往不用货币结算,也无法被传统GDP所统计。四是新经济的生产或服务方式趋于小型化、碎片化,如分享经济等的主体往往是个人,而传统统计往往以大中型企业为主,小微企业和个人服务提供者很难包括进来。因此,现有统计不但会低估新经济的GDP,而且更会低估新经济创造的经济福利。
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阶段特征是影响全球生产率减速的最重要原因
虽然统计会低估新经济下的生产率,但不能完全解释生产率的下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导致其对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尚未得到发挥,这是全球生产率减速的主要原因。
第一,上一轮产业革命对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明显递减。从过去的经验看,历次工业革命遵循“边际递减”规律,如果没有出现新的工业革命,原有工业革命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前三次产业革命都出现了重大技术变革,陆续催生出一大批新产业,大大提升了经济效率,在较长时间保持了较高的生产率。而且,历次工业革命具有连续性,即原有工业革命效应还未明显递减时,新的工业革命已蓬勃展开,因此没有出现明显的生产率下降周期。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发展迅速,但1980年代后发展明显递减,在1980年代全球生产率增长进入阶段性低谷。但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兴起,全球经济从1990年代开始又进入一个以IT革命为代表的长达10多年的新增长期。IT革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时间最长,效果最明显。例如,使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成为可能,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近年来,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同样是IT革命的产物。但自2000年代中期开始,IT革命乃至第三次产业革命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开始递减,新产业革命尚不能弥补IT作用递减的缺口。
第二,新产业革命尚未出现引领全局的新技术和新产业,目前很多创新仍处于孕育期和导入期。新一轮产业革命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出现了“多点突破”的趋势,但并未出现可以引领经济社会全局变革的重大技术突破。在技术创新方面,人工智能、储能技术、癌症治疗、可回收火箭等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技术和发明,但仍处于孕育阶段,有的甚至还只是一些概念,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应用更是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时间内不会提升生产率。此外,智能制造、“互联网+”等技术则处于产业导入期,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刚刚起步。目前,新产业革命对生产率的作用主要依靠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相比技术创新,商业创新门槛低、难度小、见效快、易模仿,但在提升生产率的强度和持续性方面都不及技术创新,以国内共享单车发展为例,从最初出现到市场基本饱和大约只有2年时间。
第三,目前新经济以替代效应为主,进一步拉低了对生产率的正向作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经济活动的替代。例如,新能源汽车主要改变了传统燃油汽车的动力方式,并不会像汽车诞生后带来的大规模公路建设、运输效率大大提高、城市规模扩大等巨大的创造效应,但会取代传统汽车制造业和加油站等。虽然新经济提高了效率,但考虑到对原有经济的替代和“挤出”,其净创造效应往往小于预期,对生产率的净提升作用也不明显。
第四,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具有独特优势。部分发展中国家保持较高的生产率,主要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是扩大开放引发的生产率提升,包括引入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等要素,以及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学习过程等。在这方面,越南、印尼等开放战略实施较好的国家,明显优于巴西等国。另一个是利用好特有优势发展新经济。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经营和消费模式尚未定型,比较容易推广网上商城等新商业模式。再如,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人口众多,拥有广阔市场,同时人口结构年轻,对新业态、新模式的接受能力强。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传统模式根深蒂固,新经济的替代效应会影响原有的利益格局和生产消费习惯,因此发展难度反而大于新兴国家。
从未来发展看,新一轮产业革命进入成熟期后,很可能将全球生产率拉回工业革命以来的平均值,大部分国家的生产率将触底回升,由减速转为上升,甚至增速可能超过前三次产业革命。这可能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实现:一是“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制造业”,这将推动制造业复杂化,降低制造业成本,增强制造业的及时响应能力,还将使生产小型化成为可能,从而提高传统制造业的效率;二是可能出现一些引领全局的技术和产业变革,特别是如果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被广泛使用,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分配体系乃至思维模式都将出现空前变化,这种变革的能级和冲击不亚于前三次工业革命;三是目前很多领域都处于重大技术变革的前夜,如生命科学、储能技术、量子通信等,它们有可能在同时或相继取得技术突破,广泛应用,并进入成熟期。加之不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融合,也会大大提升生产率。
在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中,中国面临重大发展机遇,有望实现“弯道超车”。为此,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争取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取得突破,引领全球生产率增长。
目前,中国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共享汽车等很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方面已经引领全球。一方面,未来要大力支持这些新商业模式出口到国际市场,包括发达国家市场,推动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国内要继续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商务模式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减少政府不必要的限制和干预,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才能,推动形成更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商业模式。
在新技术和新产业方面,目前中国在基础研究、产业基础、成果产业化等关键环节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中并不占据优势。展望未来,一是要加强政府的作用,扩大基础研究、公共技术平台等投入,紧跟前沿学科前沿理论;二是支持企业的研发和技术投入,吸引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和创新活动;三是借鉴高铁发展成功经验,一方面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当保护,为新技术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在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智力等要素。